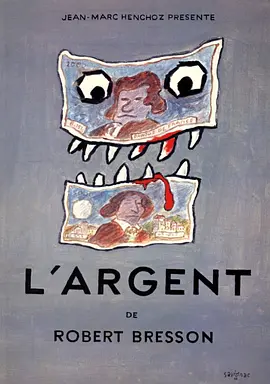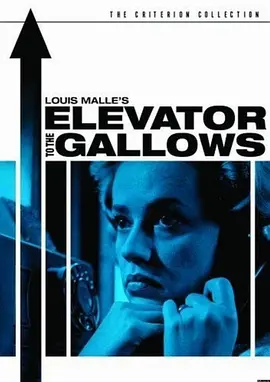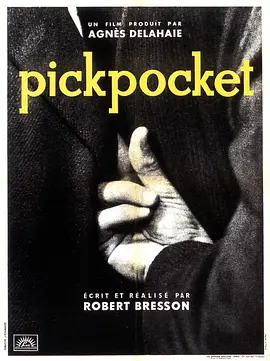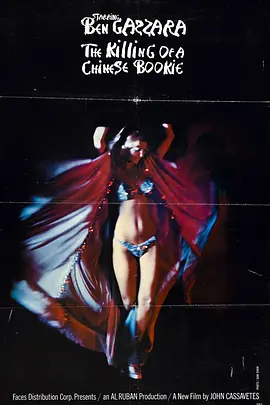|
这绝对是我不可能会忘记的电影了。
抛开它涵盖的国家秩序阶层权力信仰等等内容上的讨论,仍然有超惊人的组织框架、层次递进、呈现手法、逻辑结构等可挖,全部都是金光闪闪的牛逼,教科书式的神作,高考出题班底全来给你当私教的感觉 |

|
大岛渚在他新浪潮口味的[绞死刑]里讲述了一个卡夫卡式的作品。它看上去旗帜鲜明地在反对死刑,但真正的矛头是指向民族国家这种机构的荒谬。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解释杀人犯的动机,在这里影片兜了个大圈子。在想象中重建现实这一动机不仅费解,而且被生硬地嫁接了进来。光靠爱是无法为谋杀正名的。 |

|
像一块扔向日本社会的石头,要的就是这股劲 |

|
冰冷的行刑室,这是齐泽克口中客观暴力的施展场所,是规训的最终环节,是不合格社会机器零部件销毁的垃圾场。这一切都要最终回溯到人类符号系统的最高暴力—法律。也可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大他者。你的行为无时无刻不被大他者影响,因为你身处符号系统之中。而R在绞刑后没有死亡,并以失忆者的身份复活。因为没有记忆与身份认同,管理者们教他说话,教他词汇、重塑犯罪现场唤起记忆,只为换回R的记忆与灵魂,以此来再次定罪绞死。R如同一个脱离于象征界的真实实体,重新接受符号系统的阉割,并接受他的命运。结尾被绞死后空空如也的绳套所揭示的,正是肉身早已死亡,第二次的绞刑所要消灭的是被符号阉割后的灵魂。这是影片大致的框架,之中填充的诸如R日籍朝鲜人的民族认同缺失、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现实与幻想重合导致的暴力等元素也都颇有反思性。 |

|
内景幻想中的演绎真实,外景现实中的梦中幻想,大岛渚用尽手段【开头的介绍,三一律,重复镜头,照片的回忆,超现实】混淆真实与想象的界限,以此意图解释人类内在纯粹的自我存在困惑以及外在种族社会国家裹挟下的自我认同困惑,最后把观众也拉进这场谈论中。纪录当下并凝练升华观点的最佳拍法。 |

|
被处以绞刑的杀人犯没有被吊死,醒来后丧失记忆。为再次实施绞刑而不得不唤起犯人的记忆。由此引发一连串的叩问。死刑的意义,国家主义,在日朝鲜人的歧视,神的存在与否,现实和想象的不一致性等等,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全盘人物的符号化。(无字幕,择日重看) |

|
身披荒诞喜剧的外衣,涵盖的话题和内容却异常丰富,斗室内的调度和站位编排精心,有强烈的戏剧舞台感。1、当灵魂和肉体分离,是否还可以确认“人”的存在,即——所谓“人”究竟该以何种标准评判;2、幻想在现实中所占的地位,当潜意识超越了现实,两者的界限不再分明;3、个体在宗教范畴和社会意义中不同的定义;4、朝日关系永远暧昧纠结的镜像;5、一桩社会案件折射的历史钩沉。 |

|
一点不抽象,像一幅闭合的电路图,关键在于大岛意在用超验手段揭示历史的辩证过程,而不是将历史事件偷换为超验现象,或一种集体幻觉。形式极端混用极不对称极不统一,先用戏剧表演推翻纪实电影,再用超验段落推翻戏剧舞台,简直和推理过程高度和谐。历史的身体并未被宣判、被绞死而是亟待推理,一如《感官世界》中亟待重铸的爱欲,大岛每一次都能用信念杀死唯心史观与色情的虚无,用信念将历史与爱联结。 |

|
题材发人深思,曹杨影城,全场在笑的是傻逼。观影体验,好起不来,看完难受。 |

|
十分《圣经》,R 在官员面前复活即耶稣在门徒面前复活,而耶稣的复活需被「见证」以增加其可信性和威力,正如《圣经》中不断描写谁谁看见了耶稣,本片也反复强调谁、什么时间点看见了活的 R;复活使 R 从具体的人变成形而上的比喻,其复活被见证过才具有神性,而其见证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其追随者。在暴力机关迫使 R 再次成为 R (具体的、有罪的人)的过程中,R 反而逐渐更具有一种象征价值,那就是将剥夺生命权的死刑与剥夺民族性的殖民联系起来,反死刑必先反殖民。片尾处越是「虚幻」的场面越贴近取材事件「真实」,这个处理十分有趣。可惜头半小时里我又昏过去十分钟,看完脑瓜子嗡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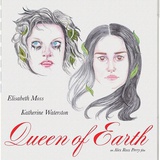
|
和《桃色案件》,《十二怒汉》连起来看,会非常有意思。但远比美国人的评书流高级,高级太多!静态的剧场,张力太足,终于冲破了房间的局限!如今村昌平般野蛮生长,如筱田正浩般仪式布景,如铃木清顺般意识跃动!之前太看轻大岛渚,我错的离谱了! |

|
只有我一个人认为是探讨民族问题大于法理道德问题吗 |

|
只有日本人拍得出的电影,极荒诞又极现实;充满符号的对白还很自然,大岛渚甚至还做到了喜感,经常逗得我捧腹。又是卡夫卡式的现代寓言,但难得的不cliche不招人烦。室内场景调度精确,抽象空间里保持真实性,虽小成本但绝对更适合大屏幕;时间不长的室外场景随意炫技,具象空间创造梦幻感,妙不可言~ |

|
7/10。在R终于记忆起自己的朝鲜人身份时,镜头缓慢后退,圆形的绞索就在头部上方,这和莫名被官僚杀害的女学生,被放入棺材的身体上覆盖着一面太阳旗,形成了绞索=国旗的同构图案,意思为国家体制的名义下战争和杀人的禁忌变得有理有据。大岛渚的构思起初是官僚们说服R再认罪的可笑尝试,密闭的刑场和糊满报纸的室内搬演,在R参与到姐姐的回忆后,画面转为静照呈现了贫困的街景,再景别不断缩小到R失神的脸,暗指体制对人的无言压迫,早已死去的女学生复活,身份变换为R的姐姐,而不认罪的R在门口被象征体制的强光阻挡了自由,最终执行绞刑后身体消失,都是个体的民族身份被国家体制所定义和取消的控诉,并用R和女学生骑单车跌落河边后不断翻滚又相依于小船中央的浪漫影像,表达以爱反体制的身体自由。但一层一层搬演场面的积累,突显了结构的过分冗长。 |

|
誤解大島渚惹。 |

|
一开始还以为要讨论死刑制度、接着变成重演案发经过和讲述在日朝鲜人杀人的心理状态、谁知画风一转又变成日本帝国主义啊、朝鲜民族如何如何……歧视问题等等。最后竟然得出了一个神结论死刑和战争一样,都是为了国家而杀人。真是时代不同啊,就这个狗屎结论要是现在的导演拍的,估计差评一片了。 |

|
不喜欢里面的政治色彩 |

|
小成本这事也能出来吹牛逼了,你看那移动镜头抖的。前半段密室戏行,不过直觉告诉我敕使河原宏拍会更有意思,后半段干脆弃了。 |

|
大島渚十分高章的民族、政治寓言!絞死刑終究把握著R肉體和精神的生殺大權。電影始終充滿著一股「干預」的力量。從敘事策略或者形式上看,那是時空和角色的交錯;從內容劇情上看,那是律法上人道主義的干預;從更深層次上看,那是民族和國家的互相干預。若干個分鏡還是對這種「干預」起到抵觸了。 |

|
比[被迫情死]强了好几个档次,姐弟那一段太神了 |

|
当大岛渚尝试将主题上升至国家和历史仇恨,以R个人的成长和犯罪经历作为死刑废存问题的论据就显得捉襟见肘,狱警说R有罪是针对两桩奸杀案而言,R说自己无罪是针对日韩情绪而言,他犯下的是针对人的罪行怎么能被国家这个抽象概念处死,这无疑就是诡辩,不妨把这当做是大岛渚的激进左翼表达,检察官让他开门看到的就是国家概念的具象化,你看他还是认可了人心的 |

|
R的肉體拒絕死刑 |

|
#cinémathèque大岛渚回顾展# |

|
类似卡夫卡《审判》般的异化司法模式,拉康式自我审视与自我认同机制的应用。国家机器的荒诞丑恶。看过大岛渚这部影片后再去审视《禁闭岛》而仍旧采用“治疗论”观点的人是幼稚的。“不是我们要杀你,而是国家不让你活”杀死R的过程中,基督教、民族主义、性等都成为帮凶。更包括看这部影片的你 |

|
-极具广度与深度
-民族主义去对抗军国主义,用魔法打败魔法
-侵略殖民过朝鲜的日本官员去跟朝鲜人谈论罪行也是很幽默的
-个体与国家机器的关系 |

|
拍得非常精彩,堪称逻辑谬误大全 |

|
5/5 卡夫卡式的繁复荒诞,先锋性丝毫不影响其观感,atg三个大字的出现已经令人感动,多元的人物刻画,逐层揭露的探讨话题,最后打破壁垒,对话观众,都是神来之笔。何为大岛渚可见一斑。 |

|
前半部分相当的精彩 |

|
现实主义 |

|
吃完爆米花就睡了。。醒过来再看几分钟就好想走人,想着下一场必然要迟到好捉急,但是旁边的人正襟危坐看得那么认真,简直生气。。反省精神是不错但我是不太能接受日本人这种说教啊。。哪怕开头的情景喜剧部分也觉得为了表达主题太丧心病狂了。。提醒自己get不到大岛,不要再每次电影节折腾一回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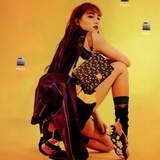
|
这电影让人绝望 |

|
7.5/10。①运用(如舞台剧般)浮夸的表演模式/调度和各种(超现实的)幽默/笑点+干净冷感且表意有力的摄影美术营造了充满讽刺性的荒诞气质。②场景变化少(后段变化相对多了很多导致影调不连贯,是败笔)、大量长镜头、少配乐、戏剧性淡、各种独白/评论剧情型字幕卡等视听技法一个是让影像脱离了传统故事片的范畴,一个是让观众在潜意识里更倾向于审视/观察角色而非代入角色(契合本片对角色/故事的批判属性)。不过,这些视听选择(除了评论剧情的字幕卡)也大大限制了本片影像力量的上限。③作为情节主导型电影主题表达不够集中清晰深入。
具体长评。 |

|
7。R死了 |

|
意蕴丰富,宛如一出激烈话剧,又带有电影才能做到的超现实诗意。对奸杀犯的内在精神和环境压力分析很到位,对国家的讽刺需多了解。解答了为啥强暴者的动作都娴熟精准一致这个疑惑,因为他们在幻想中排练过。女记者的拔高奸杀案也是幻想。现在日本朝鲜人的压力参考《大暴走》 |

|
很癫狂。。。 |

|
舞台剧风格明显,剧情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探讨了多个严肃议题,既有对死刑针对的是灵魂还是肉体的争辩,也有对在日朝鲜人生活困境的展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公权力的抨击,在这场倒带重演的死亡闹剧里权力阶级扮演的是跳梁小丑的角色,为了政绩不惜去诱导R成为了R,演员们夸张的表演更是增添了作秀的性质,室内镜头调度也很有张力,多个借绞绳作为取景框的镜头特别好,困囿感很强烈。 |

|
完全的な傑作だ!完全超越了处女作中对“犯罪”的讨论。1.个人意志的核心(我为什么是我,精神/肉体二元论)。2.犯罪完成的条件、偶然与随机(引入社会阶层的矛盾)。3.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战争中的帝国主义问题、战后的残留)。4.宗教问题(杀人是否为原罪)。结构:戏剧(分幕、戏中戏、旁白、间离) |

|
此人思想深度极深,我方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你对线。四星观察。你可以不知道,但你还是你。哲学的东西妖氛莫测。 |

|
【SS】充满洞见的寓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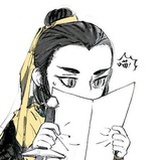
|
其实前半段荒诞得挺欢乐的...讨论了许多问题:死刑,唯心,民族问题还有犯罪心理学。 |

|
一部充满了想法与内容的批判式电影。但细细思索,片中的人物都有各自地域和民族的缺陷和禁锢,因此思想意识都颇为偏激。姐姐和弟弟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在重塑弟弟人格的过程中却又印证了他还有更多的忧愁和悲伤,他的无辜与悲悯之情(与当下发生的滴滴司机案件做个遥远的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凶手的背景和犯罪意识,但他的犯罪就是犯罪,我可以选择不原谅)。看到最后实在是太累了。大岛渚放了太多内容。这个仪式和形式都让我想到了《十二怒汉》,虽然走向完全不同。 |

|
看电影的诸君,也真谢谢你。大岛老师是懂杀人诛心的 |

|
楼南光好吵 |

|
笑到流泪(虽然最后的无罪论并没有说服我),小剧场的男纸们就是如此足智多谋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通过脑内漫游走出陋室突破单一场景话剧电影的幽闭。一堆老男人穿立领校服简直噩梦场景。记得是Atg投拍电影第一号?超低成本。 |

|
很好笑 |

|
大岛渚的诗学,如果存在的话,就只能是“政治”。同时大岛的影片也常常因此失去“天真烂漫地大笑”的朴实面向,其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于智性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思辨之中,正如《日本的夜与雾》之中的非专业的表演风格与粗糙的镜头起落间如齿轮般契合的穴式结构那般异化为一种思想的索引标记。只有极少数的时刻与为数不多的场合中,大岛才会拿出那根修长的纤细羽毛给观众挠痒痒,“毛”是演员,那么中间那根茎就是场面调度——也就是《绞死刑》。
更重要的是,大岛从不为角色擅加修饰以契合某种自然主义的诉求(这点与帕索里尼对自然之“然”的厌恶有异曲同工之处),你可以说是演员极高的出让程度让自己的整副身体都转出为导演的书写工具,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大岛使他的木偶保持原貌,我们甚至还能听到其关节活动的咯吱响声。
2024.2.4 |

|
老实说看得我有点心烦、不怎么喜欢这部电影诶、但是拍的确实好、只是这个故事~ |

|
#Alfie 没有中字看得我一知半解,但是非常surrealism,构图极其工整,前半部分是很荒诞离奇的喜剧,后半部分是严肃的人的身份认知内核。很喜欢。 |

|
如果复苏后的R是缺失了原有灵魂的躯体,那么最终处决后绞绳中的空无一物大抵可视为无法凭借身体被惩罚的清白灵魂。清白,并非道德意义上的无辜,毋宁说是符号秩序中的空白和短缺,当幻象-客体把自己变为空白 ,律令-大他者的象征性建构赋予主体的空位(没有身体的绞刑架)便毫无意义,主人能指沦为空洞能指;它以顺从审判的方式逃脱了刑罚,因为审判/律令/国家/意识形态乃是以前意识形态的不可能的内核为起源、根基和支撑的,R以倒置返回起源,获得了彻底的自由-空无,某种意义上讲,最后时刻的R是律令的祖先。只要那个想判R有罪的实体与把战争和死刑合法化的实体是同一个,R就是无辜的,R因其无辜的颠覆力量被审判和处决;在遵从法律的判决、印证律令的权威之前,它已然以其无辜成为法律的史前创造者。遵从法律就是证明无辜。R的无辜在结构中具有必要性 |

|
电影形式上最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内核的作品,不愧是大岛渚,即便我在疲惫状态下错过了一些台词,但还是被一些关键场景打动。 |
![豆瓣评分]() 8.2 (3517票)
8.2 (3517票)
![IMDB评分]() 7.5 (3,470票)
7.5 (3,470票)![烂番茄新鲜度]() 烂番茄: 86%
烂番茄: 86%![TMDB评分]() 7.50 (热度:3.83)
7.50 (热度: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