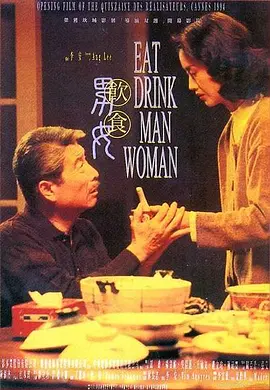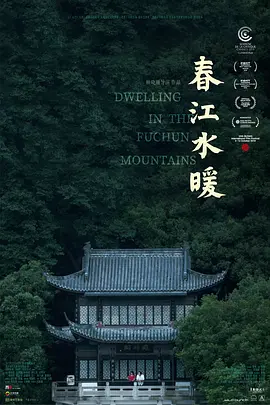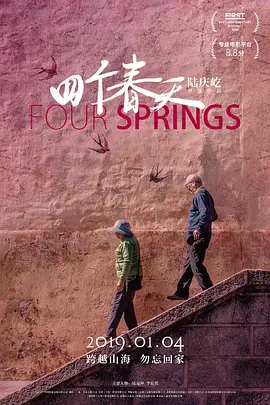|
我分不清楚,刘陆的崩溃、痛哭是我们基于表演理解的“真”,在真实的家人眼里是否是“假”?; 王庆丽的“漠然”和“虚伪”是否才透露透露了家庭的本质,不得不拧在一起相互拖累的自我与家庭的现实距离。 |

|
刘陆问王庆丽你怎么能十年不回来的场面在我心里必定载入世界电影史。它完成了一个我一直以来大为期待的事——人与平行时空的自己对话,来看看其他的自己会如何选择、如何取舍,只不过我没料到这一幕果然成真时会如此残忍。人物在这部电影里释放的情感,借助戏剧化的呈现,达到了难以超越的“比真更真”,回想自己拍纪录片的历程,实在是叹为观止。 |

|
隐形眼镜都给我哭掉了 当生活与电影互文 偶然的温馨成为片名 庸常的遗憾被深解为宿命 电影让每一个人重新审视生活 |

|
东北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语气。不知道这对于东北人而言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惩罚。大鹏说想拍天意,这确实是天意,只不过天意突然拐了个弯变成了这个样子。08年大鹏还是个小伙子,随便拿DV拍着玩,十几年后一切都变了,时间最沉默也最苍茫。人间本身超越一切虚构,更何况是中国的人间。《四个春天》也好,《吉祥如意》也好,打动人就因为拍摄人间变数和处于变数中不知所措的人,以及不知所措之后还得在一声叹息里收拾收拾继续生活的劲头儿。唯一的外来者演员问十年没回家的女儿,为什么十年没回来。那段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生活的选择是不可总结成一二三四的,都是偶然和碎片连缀成线然后就度过了十年,外部永远无法明白处于一种生活内部的人为何做出那种抉择,所以外部的人易于下道德判断,而内部的人通常只是沉默和苦笑。大鹏好在不做判断,只轻声叹息。 |

|
some thoughts:刘陆作为职业演员,无论怎样进行自然主义的演绎,和真实人物之间总有间离感。这种间离感来自于演员的感受力更强,故事会引发他们强烈的情绪和反应,而对素人来说这不是故事而是生活,他们有着被生活打磨过的钝感,麻木、不执着原因。刘陆会问丽丽,为何你十年都不回来。作为演员她需要知道原因。作为真实人物,丽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中间横亘着或许更长时间的纠葛、无奈、回避和冷漠。她只能在冲突爆发时去玩手机。 |

|
带我妈去看的,后悔了,这鸡毛蒜皮天天都在经历,好不容易休闲坐电影院两小时还得再感受这些...😥(PS如意里好几个大鹏的镜头也太自我陶醉了,不过大体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哎可偶尔的感动实在有些隔靴挠痒的廉价。真的能改变什么吗,扎进去看一头就撤了。对真正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这样的记录或许真诚,可实在太轻了,轻浮,可以这样形容吗) |

|
想不到大鹏拍出《吉祥》,更想不到《吉祥》之后,大鹏拿出《吉祥如意》。将短片发展成长片是青年导演的惯用方式,大鹏的不同在于《吉祥如意》直接套用《吉祥》。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将成片与拍摄并列,相当于设局和解谜,至于哪里真实、哪里虚假?你自己去辨别吧。 |

|
会议室的紧锁眉头、咖啡馆的飞扬手势,镜头只要长时间落到大鹏身上,虚实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滑向一种故作真实的虚假。 |

|
伪记录再套一个伪记录,我没看到真诚,反而觉得更虚伪。算不算贩卖家人情感变成商业大片? |

|
听到生理盐水和呼吸氧包,失去记忆的儿子哭了。看到燃烧纸牛和匍匐孝布,宛若孩童的父亲笑了。年夜饭系上家庭死结,电视机少了温度显影。导航说,请在适当位置掉头,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已拥有另外世界的子女,陷在文武香贵里的吉祥,随齑粉步入轮回的姥姥,原来生活无法掉头,才在门后贴上吉祥如意。 |

|
之前在金马看过短片版的《吉祥》就很喜欢,如今看了完整版的《吉祥如意》,也看出大鹏对他创作可能的更多尝试,资料馆那部分还是很有意思的。归类的话,这应该叫融入剧情片段的记录片吧。重看还是觉得一家人在饭桌上吵架那场戏厉害,太真实,太熟悉,所以还是生活本身最戏剧性啊。 |

|
一半吉祥,确认他还活着;一半如意,接受他已死去。智商退回四五岁儿童的老人,要如何捕捉他的内心感受?将他完全放逐。
前半段以摄影机在场—不在场—在场的闭环,将对三舅生命的解释权如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而其本人似乎已不再参与自己的人生,无论是那些漂亮的言辞,或不堪的攻讦。假意温馨的合影是对无疾而终的争吵最好的回应。空镜扫过冷寂的村庄,不是三舅望见了雪,而是这场雪证明了他依然活着。
后半段迅速抽离,开启旁观,如站在玻璃罩子之外重新解构这个故事。他在罩子里的活着,恰好映照了罩子外的我们对他死去的默认,从我们的繁华世界将他顺理成章地彻底抹去。
大鹏用一双冷眼观察,当他装不下去的时候,便是这部电影甚至这个世界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瞬间。 |

|
期待过高了。《吉祥》中的炕上家庭戏值五星。《如意》里的大鹏形象却看起来更鸡贼、更刻意了,宾馆关门痛哭是不是一种表演?真丽丽假丽丽同处一室是不是一种安排?……观影时忍不住反复猜想这些情景的动机,完全削减了真实的力度。如意并没有对影片做更深扩展,反而是无力的复制,证明了导演的才华有限。 |

|
如果说大鹏仅仅在叙事结构、拍摄手法上打破国产片的格局,什么第四面墙、层层嵌套、戏中戏中戏之类的,都这不算什么。最主要的,他通过想拍一部关于姥姥的影像,无心插柳完成了一部中国家庭浮世绘全貌,这才是电影如虎添翼的地方。“树倒猢狲散,老人没了,一家人就很难再聚齐了”家人的牵绊、负担和义务,沦为现代人的亲情之殇。“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十年不回来啊”在城市打拼和回到乡里判若两人的我们,又何尝不被刺痛?老人越老越孩子,那句“三哥哭了、三哥哭了”把我的全部防线彻底击溃。大鹏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柔弱与残忍,刨根刨底地,为我们呈现了他最私人的影像(镜头下都是他最亲的家人)。坐在电影资料馆看这部,当画面逐渐拉伸到资料馆的画面,梦一般从电影穿到现实,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叹为观止! |

|
批评过大鹏之前的烂俗喜剧,这与我在一些瞬间被《吉祥如意》打动,并没有任何冲突。观众或许应该知道,资料馆那场放映被告知要录影拍摄,否则镜头不会那么准确,跟到导演和主演脸上。返乡的《吉祥》,加上了纪录侧记性质的《如意》,令许多观众可以易换位置,去思考电影与现实,一个身体里住着两个不同人的形影关系。不过,我认为光有《吉祥》《如意》还不够,还要加一部《映后》。当然,拍出了“一个春天(节)”的大鹏,是可以去追求口碑与票房,毕竟,全家人一起演戏,表现都还不错。抛出中国式家庭问题之后,原型不想接,主演不想接,导演也不想接,观众得接。但观众是否一定要接呢?至少走出电影院之际,我并不带着电影回去。 |

|
刘陆是假丽丽,但有的时候她比真的丽丽还真。
尤其是二大爷有点太咄咄逼人了,以至于她当场给他下跪磕头。
看到这一幕,你能说她是假的丽丽吗?
这个时候,她就是真丽丽,而且比真丽丽还真。
因为此时真丽丽反而不怎么关心这件事,而是在玩手机。
刘陆磕完头后走出了片场,来到了隔壁的房间。
此时刘陆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正是丽丽,而刘陆当时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
于是真丽丽和假丽丽就这样同框了。
假丽丽此时是五味杂陈,而真丽丽反而成了局外人,好像这件事跟她没关系一样。
两个丽丽同框的镜头解读空间太大了。
首先是演员入戏太深了,甚至变得比原型人物还更真实。
其次是演员和原型人物面对四姊妹为父亲吵架的反应截然不同,这不禁让你想问,到底什么才是真实?
更妙的是,这场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完全没有事先的编排,没有任何设计。 |

|
以我肥头大耳、惨不忍睹的亮相,完成了“吉祥”与“如意”的魔幻转场,这事儿本身就很魔幻。 |

|
说点跟电影无关的,并不觉得真丽丽看手机是冷漠的表现,反而是无力无奈下的选择看手机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像是奔波了一年的社畜,每当过年的时候就想着回家一样,在外面磕碰头划下的伤口,是需要找一个无须掩藏自己的避风处疗愈,所以过年回家就显得那么的珍贵和必要。 |

|
特别好。《吉祥如意》更像进一步完善了大鹏的艺术人格。《吉祥》和《如意》两者互相补充,《吉祥》是虚实之间的试验短片,《如意》是一封写给自己和三叔及姥姥情深意切的书信。在《吉祥》中看透了人间的生老病死,在《如意》里生活继续下去还要靠孑然的彳亍。 |

|
我现在尚不能概括看这部电影的感受。
它用《吉祥》带人入戏,又用《如意》完成了一次巨大的间离。
它用一个演员串起了前面的“伪纪录”与后面的“真纪录”,但这个演员同时作为一个“间离因子”,在前半部分,她努力入戏,却依然有表演的痕迹;而在后半部分,她无法出戏,乃至于对真实人物发出质问。
这部电影最值得探讨的,就是它的形式,它游走于真实、虚构、纪录、表演之间的暧昧性。
你会不由得思考现实与搬演、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并最终明白,比起人来,老天爷才是更具“作者性”的导演。 |

|
文武香贵,一二四五,就是没他自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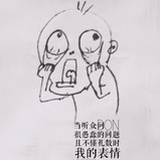
|
相当好,没必要提《摄影机不要停》和《纽约提喻法》。大鹏拍的不单是的纪录片或伪纪录片,而是一截影像,一段命数。年夜饭一场戏,王家人愈吵愈烈,丽丽”逃离镜头。摄影机扫过一面镜子,“丽丽”握着茶杯出神,丽丽倚在一旁看手机,可以说,刘陆在《吉祥》部分的入戏,多少造成了作为观者的我的出戏,但刘陆毕竟不是要成为大鹏或是丽丽姐的角色,“丽丽”是我们在虚实之间通灵的媒介。 |

|
《吉祥》是很像剧情片的纪录片,《如意》是很像纪录片的剧情片,它们是完整的一体。甚至连北影节的放映都参与其中。第二部分跨越时间,很好地解构了前半部分,解答了观众对《吉祥》中真实与虚假的模棱两可,这就是结构发挥作用的地方。虽然是用类型、结构带来新的叙事突破,但它还是从人物、情感出发,步步深入,最终抵达人类情感深层,带来共情,感受普世亲情的价值所在。 |

|
这不是电影,这就是纪实文学。现实是中性的、琐碎的,而艺术是情绪饱满的,是凝练深刻的,艺术远比现实更现实。这或许是真丽丽玩手机,假丽丽入戏深的一个原因。 |

|
假丽丽崩溃地离开现场时真丽丽只是冷漠地刷着手机,大鹏利用蒙太奇创造了一个孝顺的女儿,真假之间遥映着人间百态。前两周奶奶离世,丧宴和各家分钱的场景和王家也没什么两样。太佩服这种剖开生活的勇气了,一团和气下是暗流涌动的算计,看着那些暗戳戳的对话好像自己都窒息起来。 |

|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筷子洗洗碗。 |

|
不太行。吃饭那一段不错,很真实,散场后我和老陈聊了好一会儿,都好像在那场戏看见了自己身处的大家庭,但女演员一磕头我就立马想翻白眼。还有,女演员质问现实中的女主为什么十年不回来那儿我也白眼翻天上去了,你入戏可以,但对她来说,这是她自己的生活,她他妈自己的生活。 |

|
观影过程中一直困惑对大鹏的定位,直到最后刘陆在吵架声里走进房间抽烟,一旁她扮演的丽丽正在玩手机,俩人合起来就是对大鹏和这个项目最好的定义吧。 |

|
哭掉了五张纸。。五星给敢于在镜头面前直面和剖开家庭内部的不堪和暗面的勇气。而家庭就是这样,一团和气下涌动着算计和埋怨、逃避和麻木。它们通常在两种情况下爆发。一是过年时,二是葬礼后。爆竹燃尽,逝者入土,生活继续,吉祥如意。 |

|
镜头怼着酒店走廊的墙壁拍,大鹏在房间里嚎啕大哭,这是表演吗,他是难过还是忏悔?大鹏的这个动作就像是整部电影的一个缩影:他把自己藏起来了,又把家人的反应全盘托出来成全他电影的戏剧性。我不认为这种刻意模糊虚实界限的电影值得表彰,电影拍摄过程剥削、消费家人的行为,反而应该引起观众的警惕和思考。 |

|
電影是好看的,大鵬的親人們在鏡頭面前呈現了誠摯和真實的感情,演員劉陸則在前半段一直格格不入。只是看這戲的觀感其實蠻像看《四個春天》,只覺創作人想拍一部牛逼電影的慾望遠勝於對於身邊人的情感;又或者說,能拍和剪出這樣的戲其實需要異常「殘忍」的心。當鏡頭中的大鵬常常流露出刻意和非刻意的表演痕跡時,我恍惚於他到底抱著什麼心情在「表演」,而「表演」裡究竟又有多少真實的感情。 |

|
《吉祥》与《如意》,一个偶得,一个天成,摄影机退回到观众席,嵌套结构的重合/分歧,微妙映衬出所谓「戏剧」与「现实」在同一事件上的不同着力点。不带任何预设或做任何功课地去看,会引发在院线看到此类作品的惊喜,打破真实/虚拟界限壁垒的手法可能并不新鲜,然而创作者置身于其间的主观代入感赋予了本片独有的悲凉沉浸感。一个大家庭走向树倒猢狲散的必然结局,人生都是渐行渐远,人生就是不断做减法(“不可能再有这样的聚会”,并无reunion),摊开的难堪困局仿佛是每一个普通家庭都曾面临的两难。
在火光的映照下,在雪地的踽踽独行中,那颗封闭的心似乎也随着母亲逝去,即使隔着沉睡几十年的蒙昧意识,他仍坚持着“明天找母”——全片最泪点之处。
被刘陆圈粉。 |

|
三流导演,四流主持,不入流人品 |

|
拍的就是我家的那些破事,一样一样的。年夜饭那场戏,二嫂说了句“拍你妈的”愤然离桌,这就是我的观后感,这些破事有啥好拍的。 |

|
最后的VCR里,王吉祥口齿清楚地说出了“文武香贵”、奶奶精神矍铄地穿着红毛衣,在镜子里看到端着dv机的大鹏,戳中了。奶奶拉来门,说“这个好”,指着门后的“吉祥如意”。 |

|
这是一部即兴电影。命运推了大鹏一把,大鹏用电影把这股劲发挥到了极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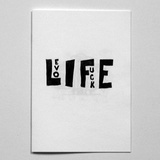
|
三星半。大鹏很聪明,这种聪明暗含着一种预设的道德立场,让他的作品有一种看似很真诚/虔诚的力量,但背后潜藏的是人性根基里的冷漠与偏执以及算计,即一种非人性/非人道,这是很残忍的,因此他的聪明背后暗藏的是一种“鸡贼”,但这又是符合懒得/无法独立思考的大众狂欢心理的,这从商业角度来说也无可厚非。最后,刘陆不错。再ps 片尾感谢名单里出现了圈内同样以鸡贼驰名的人物,哈哈哈,真是非常大鹏了。 |

|
这tm就是摄影机不要停啊,观影量这么少吗,就在这捧上天吗? |

|
手机已经不够表达我的愤怒了,必须到家换电脑,难得有几次恨不得豆瓣出负分机制的时刻,我想打负八百分。刚开始以为只是伪纪录片的形式,毕竟现在也不少见,然而当画面定格,切到下半场导演的脸上时,我懵逼了,出现影院里的观众提问环节时,我以为放映事故了,到开始从头讲起拍摄缘由以及拍摄过程时,我生气了,特别是导演站在姥姥家门口知道姥姥过世后一阵沉默,下一秒摄像机像是自己有生命般地自动出现在导演住的酒店房间门口,里面传来导演长达几秒钟的痛哭声时,我出离愤怒了!而在知道原来三大爷的女儿不是真人出镜、而是请的演员出演时,我泄气了,原来正片里最写实的那幕家庭大戏竟然也是夹着个外人演出来的,我还宁愿不知道这些事情,而那场演员质问真人为何十年不回家的特写当然是最让人生理性厌恶的,所以我愤而离场了。 |

|
看得我挺生气的,看不出什么探索、实验精神,我只看到一个在商业中眩晕的人的猛然惊醒。《吉祥》的伪纪录片里无时不刻不透露着强烈的情感渲染和商业打磨,摄影机的目的性太强了,片中没有一个人物,只有吐字的情绪符号,每次特写给到女主我都觉得自己被强奸,分镜屡屡有东北电视剧观感。《如意》一出来,简直吊打《吉祥》,能好好拍个纪录片为什么不直接拍纪录片呢,这不拍得挺好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定是和《吉祥》挂钩的,一想到这,我就觉得虚伪,彻底的虚伪,满屏的虚伪。看到最后,没有半点感动,所有的质疑都变成了愤怒,摄影机,电影变成一种挑逗生命的玩具,两部分中间还插入电影院内观众落泪的镜头,我他妈吐了,作我觉得自己被反复强奸。要看到生活,要思考影像,就放下那些浮躁的小聪明吧。《四个春天》不知道比这好几十万倍了。 |

|
有一些抱歉。对于这样一部真实的片子,我不认可它的真诚。反而觉得伪善。可能我对于表演太敏感了,前半段刘陆的表演和后半段大鹏的表演,都让我感觉到一种“对于悲痛”的粗鲁的展示。我这样说可能也很粗鲁,我很抱歉,但是这就是事实。刘陆对于那个女人的反感,正如大鹏试图去讲什么天意。都是极其表面的自作多情。实际上但凡大鹏再好好拍拍那个原型人物,而不是批判她,我都会改变我的看法。因为他太多的价值判断,太多地立场选择,而没有真正的悲悯——真正的悲悯是走进她人的无情,寻找那个“无”的原因,而不是给一个镜头让观众瞧瞧,我多有情,她多冷漠。这太粗鲁了。这个片子前半段的三舅是多么精彩,可惜全被导演的自我感动破坏了。真的很可惜。我现在理解了大鹏为什么要“站小四”,因为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世界:必须站队。唉。 |

|
让人不禁想起前些年的《喜丧》,《吉祥如意》差的是一个合适的观察位置。后半段本应打入道德模糊地带,但因为对导演本人的保护而显得有些“隔”。 |

|
一部难以复制的、受制于意外却也成全了偶然的元电影。前半段的[吉祥]是职业演员打入大家庭代替现实人物“受难”(颇有赫尔佐格[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之味),虽难以定义,但大体仍属纪录片风格的剧情电影,并间或插入(提问者藏身于摄影机之后的)对真实家庭成员的访谈,为观者渐次拼出前因后果;后半段以猝然后撤显露出影院机制与短片映后问答开始,以抽离的姿态呈现影片摄制过程,这一部分依旧超越了类型框架,因为并不止于纪录片式的幕后花絮,而是以碎片化的形式补全甚或修改了“主线剧情”,直接干预观众的认知与读解。影片的私人性非常强,但对中国传统乡村大家庭与城市独生子女小生活间的矛盾的展现却足以击中每一个人,毕竟,血缘羁绊人情要求与异乡打拼身不由己的冲突,牵系着无数家庭。PS:两段英文片名(final)reunion很点睛。(8.5/10) |

|
挺一般的 只是没想到是大鹏拍的 |

|
D / 假如《如意》对《吉祥》的补充在于建立起大鹏的视点,那《如意》本身的目光从何而来呢?假如在叠加叙事层时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视点隐形,让自己成为真实的天然占有者,并以这种占有决定虚构部分的真实性,那试图打开的出口就再次被封闭了——影片也就成为了自证“真实”的同义反复。所以全片最精彩的只是那些昭示着这种分裂的段落:比如演员对原型人物的质问,比如家人们开始争吵时摄影机的退避与逃离。然而其他都显得太过贴合,就像海报上的窗花一样精细平滑——而窗花两边本应有着极度漫长难以逾越的距离。 |

|
本质上这是部青春片。80后的青春就是这么在故乡和异乡之间,在父辈的多生多育政策和己辈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夹缝里,被蹉跎和异化了。主动的向外奔跑和被动的被拽回,才缓慢的成长了。青春如此无趣漫长和笑泪交织,变成了不敢躬身自省的埋头。挺佩服大鹏的,勇敢且有所回报。尤其喜欢今天映后他为表妹的辩护,本质上,没有谁可以评价谁,何况我们是一代人。 |

|
作为东北人这部电影完全超越了我的评级体系。所有这些片中一个普通东北家庭经历的悲欢,姥姥去世后的整套丧仪,我都完整地亲身经历过一次。我想首先讲一讲这部电影让我最为惊艳的嵌套结构。从以姥姥去世家中兄弟姊妹如何照顾痴傻的三舅为核心的吉祥篇,再到三舅在雪中独自散步荧幕逐渐缩小讲述拍摄过程的如意篇,再到整个吉祥如意作为电影呈现在我们这些观众眼前,这个剥洋葱的层级结构展现了太多普通电影无法展现的内容。而这个结构是导演大鹏一开始就构思确定的。他的进步实在太亮眼了。最令我震撼的是饰演三舅女儿的演员刘陆在拍摄年夜饭吵架戏后崩溃大哭。尽管她曾直面原始人物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问,为什么十年都不回老家看看爸爸,并最终得到了沉默的回答,她无法认同这个人物,但她真的把自己放进了这个复杂的情感漩涡中。这个片子,值得一看。 |

|
哭得一抽一抽,所谓家族之苦,是一些永远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是离开家那一刻凝结成的某种永恒。戏里戏外的互文从16年一路延续到在资料馆观影的当下,由此产生的共情强烈又奇特,对导演对观众大概都是此生唯一的体验。大鹏一定是捡到电影之神扔的烟屁股猛嘬了两口!! |

|
吉祥是一份真情,如意更像是一场阴谋。电影本来就是一个谎言,何苦再拍一部电影,用一个谎言去揭穿另一个谎言。 |

|
导演与摄影机之间的深壑,抑或是粗暴的意志与无意识的“看”之间相违。哪怕是对自身制作过程的暴露,电影仍然很虚伪。唯一真诚的理解是:当“导演”像“演员”那样走入景框之下时,是他对自己掌控欲与表演欲的双重暴露。可惜大鹏几乎没有自反到这一层。 |
![豆瓣评分]() 8.0 (44573票)
8.0 (44573票)
![IMDB评分]() 7.0 (462票)
7.0 (462票)![TMDB评分]() 7.70 (热度:2.27)
7.70 (热度:2.27)